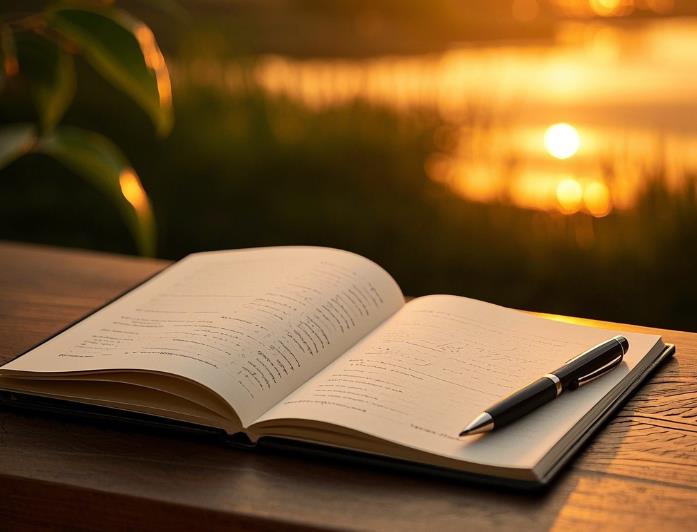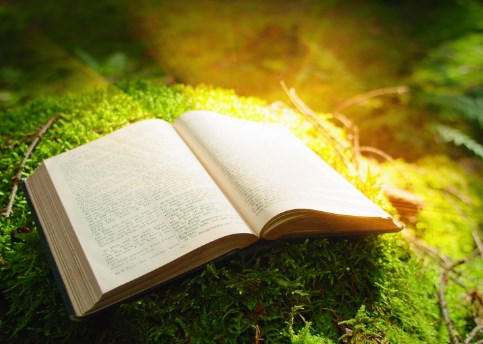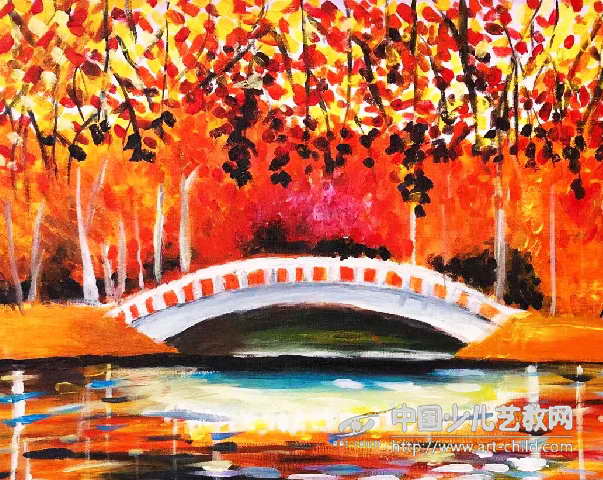看作家申赋渔怎么教女儿写作文
来源:城市商报
作者:苗恒
发表于: 2015-12-05 08:50
城市商报记者 姜锋
白俄罗斯女记者兼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凭借非虚构作品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我国非虚构文学也受到了广泛关注。提到中国近年来的非虚构文学创作,申赋渔是绕不开的一个,他迄今为止出版的六本书,都是非虚构文学。和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样,申赋渔也有着记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他的非虚构创作,也始终聚焦生活中的最普通人群甚至弱势群体,关注人生,关注人类命运,关注社会变革。他的作品因散发真实动人的力量打动越来越多的读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之前出过的书,有聚焦弱势群体的《不哭》,有写关于消逝与变迁的《逝者如渡渡》、《光阴》、《一个一个人》、《匠人》,如申赋渔自己所言,都和沉重和苦难有关。
2012年,申赋渔作为《南京日报》派驻法国的记者,与到法国做访问学者的妻子,带着12岁的女儿申杭之,在法国南部阿尔萨斯旅居一年。在这一年里,他们以阿尔萨斯为中心,游历了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瑞士、卢森堡等国家。申赋渔以一个文化记者的视角写在法国以至欧洲大地游走的见闻和感受,申杭之则以一个个性鲜明、思想独立的中国女孩的视角,写她在阿尔萨斯一所国际中学读书的经历,写中法学校教育的异同。日前,申赋渔和女儿申杭之合作出版了新书《阿尔萨斯的一年》。这本书,依然是非虚构写作,但由于是观写以浪漫著称的法国,更由于女儿的加入,《阿尔萨斯的一年》成为申赋渔作品中最特别的一部,不再那么沉重,却有点轻松诗意。
谈及非虚构文学创作,申赋渔认为非虚构至少要具备三个要素:真实性、艺术性、有生命力。“我理解的非虚构做一个定义,第一是真实或者基本是真实的;第二,表现手段是文学,不能是新闻;第三是要有深度,我们的新闻是爆炸性的,烟花一样,而非虚构一定是有生命力的,过了五年以后这本书还在的话,人还愿意翻开再看。”
说到下一步写作计划时,申赋渔说,一定是非虚构。我的下“一本书,仍然是坚持非虚构写作,从一个人的流浪史,写中国三十年的变迁,写人心的变化。”
希望能够打开读者的心灵窗户
城市商报:七年出了六本书,你写作的原动力是什么?
申赋渔:我相信真正能改变自己的是一个人的内在力量,所以,我不停地写作,想将这种力量传递。我写《光阴——中国人的节气》,希望给读者一扇心灵的窗户,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读完马上可以安静下来,感受人世间的美好。我写《逝者如渡渡》,写物种的诞生、进化、灭绝本有其发展规律,但人类为自身生存而进行的强势开拓却干扰了这一进程,加速了许多物种的灭绝。这是写给小朋友的,如果小朋友对动物都能产生情感,那么一定会善待同类。
城市商报:人们说作品是作者的孩子,父母会对每个孩子都了如指掌,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本新作《阿尔萨斯的一年》吧。
申赋渔:应该说,这是我所有书里最特别的一本书,因为写的是欧洲人,大多都是欧洲的普通人,是我们以为了解其实完全不了解的普通人。另外对于他们的文化与历史,我也是带着一种审视的态度来写的。文字比较讲究,跟我前面几本书的文字有很大的差别,更讲究韵律与美感。甚至当诗来写。
女儿的那部分,比较随意,天真自然。说实话,没有她的文字,这本书就显得沉重了。有了她的这一部分,这本书,读的时候,就可以飞起来。轻盈而生动。
总之,这是我所有书里面最美丽的一本书,无论是外观还是内容,还是文字。她不可复制。
城市商报:今年你刚刚出版过一本书,叫《匠人》,是朱赢椿设计的。我注意到你这本新书《阿尔萨斯的一年》,也是朱赢椿做的设计。这是你和朱赢椿合作的第几本书?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设计背后的故事吗?
申赋渔:到《阿尔萨斯的一年》这本书,我和朱赢椿已经是第六次合作了。我的六本书都是由他设计的。这本书跟其他书有着极大的区别。因为是写法国写欧洲的,所以用了非常时尚的概念。书有外封和里封,做得都非常用心。封面上四张图,分别代表着春夏秋冬。同时又代表着“建筑”“生活”“历史”“自然”,这八个字,又烫了银,显得品位十足。朱赢椿是个极其讲究的完美主义者。所以这本书的每个细节,他都经过精心的打磨。如果只从设计本身来说,拿到手上,你几乎挑不出毛病。因为他自己就挑了几十次了。
教女儿写作文时跟着真实感觉走
城市商报:很多人会羡慕你能有这样一个契机,带全家去欧洲,一年时间,和孩子一起慢游,回来共写一本书,给孩子成长岁月留下最有意义的纪念。你是欧游之初就计划好了要和女儿一起写书的吗?
申赋渔:我去欧洲是报社派过去任驻法国记者,女儿陪同一起出去。当时她的任务就是上学读书,也完全没有写书的计划。到了法国之后,我们发现那里的生活,跟中国的反差很大,特别是她学校的生活,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她每天回来跟我们讲学校的事,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就建议她把这些事记录下来。并不是记日记的那种,而是她把她觉得有意思的人和事写下来。我从来没建议她写什么内容,她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所以,她所写的那些,是她真正觉得对她有碰撞的,既真诚,也真实。当然,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出成书,所以轻松随意,只是对生活有个记录而已。
城市商报:看了新书,很喜欢你女儿的写作,很清新。书中很用心思地将女儿写作的部分用了嫩嫩的绿色字来表现,让人联想到绿色的嫩苗。你女儿对文字的把控力挺让人惊喜的,写作方面,她受过你特别的指导和训练吗?
申赋渔:对她没有特别的指导。因为我从事写作,家里的书比较多,从小也引导她多看书,少看电视,所以她书看得比较多。作文,也只是跟她说,我写我心,有什么写什么,跟着真实的感觉走。也因为这样吧,她平时的作文成绩并不高,因为不规范。“好作文”是有规矩的,就像是做数学题,跟真正文字没关系。作文得不到高分,让她很受打击。写作,从来不是她的理想。她喜欢的时候,就随便写写。长大了到底做什么?她不知道,我也不管。过些年,总会知道。
好的教育是给孩子适度的压力
城市商报:女儿在法国读一年中学,你应该也对法国中学教育有所关注,能从你感受到的角度谈谈中法学校教育的异同吗?
申赋渔:中国的教育,是用挤压的方式,它可能将智力平平的孩子,提升到他所能达到的最高度,也可能让天赋极高的孩子,在重复的练习中,失去学习的兴趣,或错失最能实现潜能的专业方向,成为平庸之人。西式的教育,则在轻松的状态下,让平平常常的孩子,就做平平常常的人,但他们也能拥有幸福感与满足感。而某一方面有特长的孩子,可以在自由的状态下去选择,去投入自己热爱的课目与专业,自发成才。中国式教育是矮子拔高,高个子减矮,尽量往中间靠。法国式教育是听之任之,让他们自由发展。结果是有天赋的孩子更容易成长为顶尖人才,所以法国比中国更容易出顶级的艺术家、设计师等。
如果对东西方教育做一个综合考量,就会发现,各有弊端。中国的重压,某种情况是因为教育资源的匮乏和不均。法国学习的轻松,是因为国家福利高,未来不工作也能享受生活。两种教育方式,都会让国家的未来蒙上阴影。而在两者之中的那个平衡点,也许正是我们要重视的。我想,就那是在教育公平的前提下,给每个孩子以适度的压力。
城市商报:你觉得女儿经历一年的欧洲慢游生活后,有没有发生一些显著的改变?
申赋渔:没有去法国之前,她对法国更多的是浪漫的想像,一切都很美好。但是真正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生活也有许多不如意。衣食住行,与同学的相处,校园文化的融入,都是问题。还有就是孤独,没办法像在中国这样,随随便便就有一大帮朋友,还有知心的好友。在那里,也有,但相对而言,朋友只有一两个,而且感情也要淡很多。所以回来之后,她对同学之间的感情看得更重。因为在法国主要学习的是欧洲史、欧洲文化,回国之后,她主动下很大的功夫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她觉得,如果不了解,心里是空的,没有根的感觉。这些都是她自发的。其他一些变化也有,但都融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对音乐与绘画更有兴趣了,对生活里美好的细节更在意了,等等。
城市商报:经历一年的欧游生活,你对欧洲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你实际观察到的欧洲,和你去欧洲旅居之前了解到的欧洲,差别大吗?
申赋渔:第一是环境。几乎没有污染,山清水秀。每个城市,每个乡村,都干干净净。无数的村子叫鲜花村,名副其实,到处是鲜花。第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不管陌生人还是熟人之间,都彬彬有礼,在公共场合几乎没见过吵闹的,人们安安静静,很注意不去打扰别人,影响别人。当然,他们也有许多的不满意,经常会对他们的政府有许多的抱怨,也经常看到游行与罢工。而政府公务员、银行等系统,效率极其低下。你每天只能做一件事,他们还爱理不理。因为公务员是终身制的,投诉没用,也不能开除什么的,极其糟糕。
【人物名片】
申赋渔:作家、记者。著有《不哭》《逝者如渡渡》《光阴》《一个一个人》《阿尔萨斯的一年》《匠人》等。曾任南京日报驻法国记者,现为南京日报“申赋渔工作室”主持人。
分享到:
相关动态
带孩子实践,没出校门就布置作文,这样真的好吗?
2015-12-08 08:35
17173
昨天,湖北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创新研讨会在湖北大学举行,与会专家们为素质教育把脉,共谋新思路、新举措。 用实践育人,注重培养学生动脑和科学思维的能力,这种能力反作用于课本的学习,可以事半功倍。原华师一附中校长、现武汉睿升学校校长李水生用近五十年的教育经验来解读素质教育理念。他认为,教育通过实践才能发力,培养学生们能自主参与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学会设法解决问题,在实践中掌握思考和学习的能力,获得科学的思维能力比学习成绩要重要得多。 李水生认为,教育者,就应该为学生搭建这些实践的平台,例如设置光伏发电实验基地,开设航天航空选修课,在实验中,让学生发现自己的不足,再想办法解决不足,这样,他们就会自主去学习曾经认为枯燥的物理、化学等学科,这样反作用于学习,达到了素质教育最终的效果。 我常常跟老师们说,带学生社会实践,去看大自然,也就是孩子们眼中的玩时,千万不要还没出校门,就布置写作文,这样孩子们...
课内海量阅读让学生爱上作文,创作小说
2015-12-08 09:07
16565
红网长沙12月7日讯(时刻新闻记者 黄雪) 祝贺祝贺,这是孩子们写作的最大动力,辛苦你们了!12月7日上午9点,长沙市育德小学的章宏老师在QQ上给红贝网编辑发来消息。当天,章老师的学生,三年级的瞿锦玥同学的作文《大雁小狗游长沙》荣登红贝网第四期每周作文排行榜。自10月底入驻红贝网至今,就有600余学生的育德小学就已经上传高质量作文903篇。 从落后到第一 阅读就是这么神奇 章宏老师是育德小学三年级二班的班主任,长沙市语文骨干教师,更是红贝网名师专家评审团的一员。每周五她都会在QQ上发布通知:习作获得优的同学特别提出表扬,请收集好发给编辑妈妈,同时把自己的作文上传到红贝网个人主页。这期的名单上有43名同学。 我们班的孩子特别喜欢写作文,全部都是在课堂上齐刷刷完成的原创。你想象不到吧,这个班一年以前语文的平均分只有80分,比同年级平均低15分。作文能写几十个字就是很厉害的了。现在我们班的平均分是98.5分,全年级第一。热情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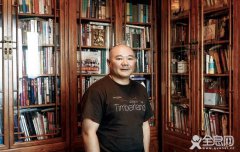
专访新概念恐怖小说领军作家李西闽
2015-12-08 09:40
18691
前不久,由福建省文学院和福建日报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作者寻找读者活动照例在福州三坊七巷的八闽书院举行,但这次请来的作家有些与众不同。 因为不满贫穷与饥饿,他8岁离家出走;在汶川大地震中,他被埋废墟,度过了人生最真实最恐怖的76小时。而灾难过后,他通过帮助别人,通过写作来进行自我救赎。 他就是中国新概念恐怖小说领军人物李西闽。为了更好地与榕城文学爱好者亲密接触,他携最新出版的小说集亮相,畅谈精神历险记,讲述别样文学路。 A 梦里闽西成故事背景 谈起自己的人生,李西闽觉得,很多时候,自己是个逃亡者。而第一次出逃,就是在8岁那年。 李西闽出生在长汀县河田镇一个小山村,尽管那里山清水秀,但故乡留在他记忆中的却是贫困和饥饿,所以他从小就想逃离那个地方。 8岁那年夏天,李西闽偷偷从家中拿了五块钱,一个人辗转来到福州。他想到福州找姑姑,其实他的姑姑在南平。 很快,带的钱花光了,李西闽开始想念家里,觉得再贫穷的家都比外面...
推荐文章

能不能用AI代写论文、代写作业?
2024-06-07

架起文学与影视沟通的桥梁(坚持“两创”·关注新时代文艺)
2023-11-24

聚焦互联网时代书店转型
2023-06-21

240万字《广东文学通史》问世!广东省作协七十芳华正青春
2023-0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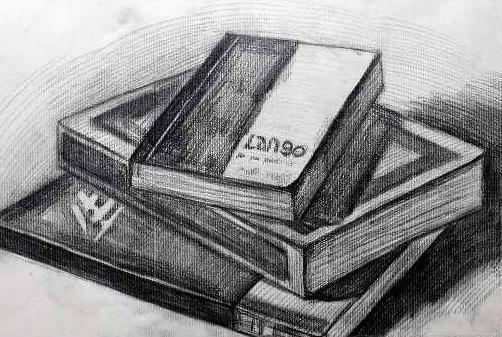
如何玩转北京国际图书节
2023-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