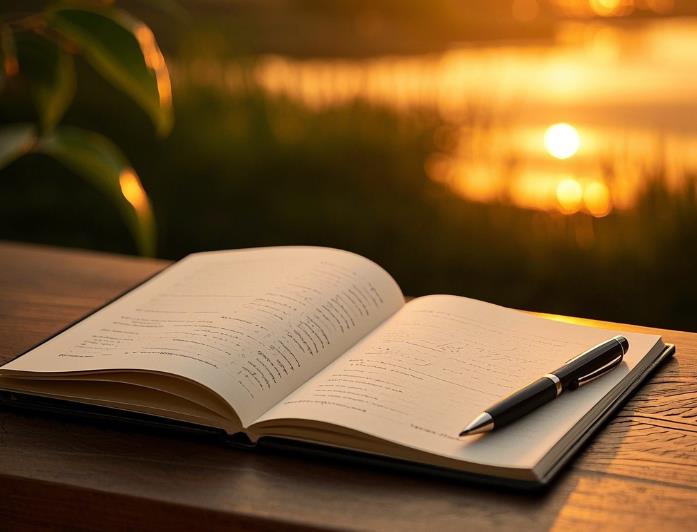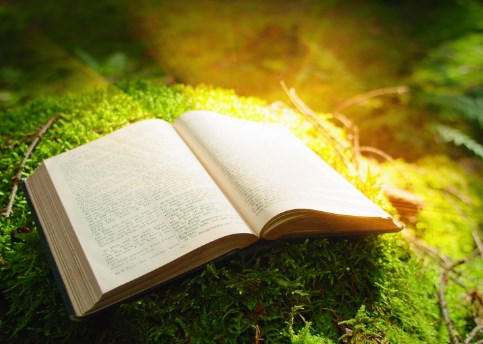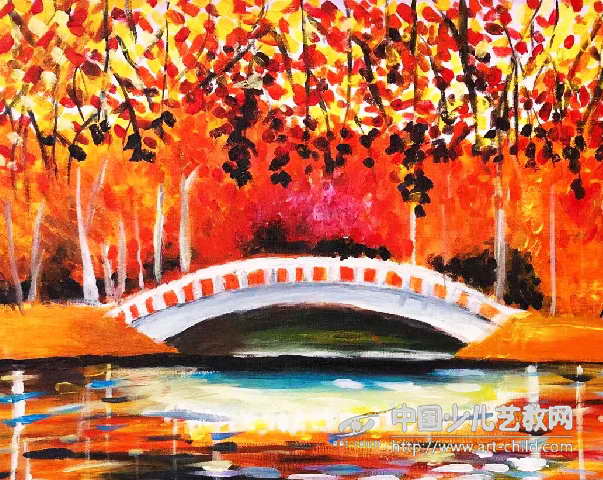专访作家张欣:做一个有趣的人
来源:中访网
作者:苗恒
发表于: 2016-01-06 11:22
“不是言情作家”
“所有的言情,无非都是在掩饰我们心灵的跋山涉水”—2013年11月小说《终极底牌》出版时,张欣说。
与她过往的题材一脉相承,这也是一部以广州为背景的都市小说。张欣生于1954年。那个年代生的成名作家作品,富有时代穿越感有之,弥漫厚重乡土气息有之,且多充满社会批判性。张欣是个例外,她写当代,写南方,写都市,写女性、欲望与情感。
从《谁可相依》、《爱又如何》,到《不在梅边在柳边》,乃至去年的《终极底牌》,张欣的小说不靠文学大奖光环也可以卖得好,常常是书还没写完,电视台就找上门来谈改编了。“喜欢张欣,因为可以在她的小说里找到隐藏在心灵角落里的自己,以及身边很多熟悉的影子。”“80后”读者Ann说。
然而正因如此,人们却容易轻看了她。毕竟,那些个城市迷离的灯火,横流的欲望,冷寂荒凉的都市人际关系构建起来的故事题材,很长时间里都被殿堂文学弃置一隅。媒体多称她为言情作家,还有说“大陆琼瑶”的,她极其不爽,一谈起来五官都有点扩张,大力拍桌子吐槽,“我写的明明是纯文学!”“他们看不到我包装之外的用心良苦!”
在公众看来,她的《沉星档案》、《浮华背后》、《深喉》,分别与广东电视台女主持人陈旭然被害案、厦门远华案和广州媒体大战隐隐相关。但张欣认为,新闻事件只是自己小说的一个个药引,小说内容纯属虚构,不希望公众对号入座。10年前她就向媒体直陈,小说家写的是人物的内心层次,不是新闻记者的平面写法。
在文学评论家雷达眼里,张欣是最早找到“文学上的当今城市感觉”的作家之一。她也是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得主—尽管试图在媒体前为都市文学“正名”,对她来说似乎比写一部好小说更为困难。
“我觉得人选择什么工作,比较宿命。”她感叹。早在小学时期,张欣就喜爱写作,这个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兴趣决定了她人生的大方向—当一个作家。而家庭背景和命运,则像一双无形的手,推动和形塑了她游走都市的叙事风格。
体制内外
祖籍江苏的张欣在广州出生和长大,她伸手指了指,“就在那个黄花岗大院”。父母都是军人,在那个特殊年代改写了女儿的命运。
“小学毕业正好碰上‘文革’,没有学上了,后来就是上山下乡运动。”她平静地说。如果当年随其他知识青年一样下了乡,中国文坛可能会多几部知青小说,却少了一位执著书写南方城市的女子。
她当然没有下乡,因为是军人家属,有机会去当兵,逃过“一劫”。一开始,张欣在部队医院担任卫生员,业余时间拼命写作,所以很快就被调到文工团,“写了很多快板啊、三句半、小话剧、小歌剧”。
很难说这样的经历对一个有理想的青年来说是幸或不幸。没错,它让一个年轻女孩绕过了很多生活上的苦难,呆在一个相对优越的环境从事自己钟情的写作训练。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更为残酷。“我们这一批作家,最初虽然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但都被禁锢在同一个文化氛围里。那时候写什么都要‘三突出’,主要人物要‘高大全’,都是没有生活细节的。不是左,是极左。”
早在1990年代,张欣就加入了作家协会,那时候加入作协是件很牛的事,甚至能改变人的命运。后来,她又担任广州市作协主席、广东省作协副主席。
然而如今,作协的口碑正江河日下。文学评论界常把作家分为两类:体制内作家和体制外作家。前者除了贾平凹、王安忆、莫言等少数派,偌大群体俨然已被贴上了“光拿工资,写不写作无所谓”的标签;而中国文学创作的重任,则被认为主要由以海岩、格非、韩寒等为代表的后者在承担。
从大院出身、部队写作到作协主席,张欣理所当然属于前者。身处这样的角色和立场,对体制内作家群体存在的问题,她既不否认,也不急于撇清,而是经由自身的经历和体会,对很多创作能力严重萎缩的同侪生出部分理解和同情。
“现在以文谋生容易多了,写专栏、出书甚至当网络写手,都很自由,只要拿作品说话就可以。所以年轻一代是无法体会到的,我们那个年代,作协有其存在的历史意义和价值。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渠道和平台啊,文字爱好者很苦的,白天做一份又苦又累的工作,晚上挤出一点时间写,可供投稿的选择也很少。我特别幸运,部队出身,不担心这个,但很多人祖祖辈辈都在农村,你想想莫言怎么出来的,多不容易啊。”
“这时作协就特别重要。一篇好作品一下子登到《人民文学》上(比如《红高粱》),就彻底改变命运了。中国作协当时有一批‘解放军作家’,有级别,有房子,可以让你专心创作。不可否认这套体系当时真的培养了很多作家。”
灵魂的重生
然而,亦正是因为那段历史的特点,随着时代变迁,很多当年的作家都被大浪淘沙留在了沙滩上。
“那时有个词,叫‘帮文学’,‘四人帮’的‘帮’,说的就是极左年代的文学作品。”张欣回忆,她很庆幸自己没有写过正儿八经的“帮文学”。她很早(1984年)就转业离开部队,开始写地方题材的作品。“第一篇小说是给《解放军文艺》的,其实就写了一个护士的小故事”,“帮文学”对她的影响可以说是渗透式的,“不是说没有,但色彩没那么浓”。
当社会开始可以张扬个性的时候,包括张欣在内,每一个当时的作家都在挣扎,拼命脱离过去“三突出”对思想的禁锢,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王蒙。
回顾张欣的创作历程,早期的中篇还是带有比较浓的理想主义色彩,强调温暖;当渐渐脱离主旋律的影响,她的大意识开始变得悲观。
或许可以这么说,当一个人开始摒除外部价值的禁锢,真诚面对作为一个“人”的内心时,都无可避免会面对现实和人性中赤裸裸的残酷和复杂。“不要说社会怎么样,你甚至会发现,最势利的往往就是亲人,包括父母,同样是自己的孩子,他们就会觉得,你当记者就挺好,他打工的,老是不行。”
“一个作家要写自己坚信不移的东西,才能写得好。”张欣说。由此,雷达评论她中期的作品:“从她上世纪90年代成形的叙事模式中跳了出来,不再‘深陷红尘,重拾浪漫’,而是向着生活的复杂、尖锐和精彩跨出了一大步,由人性善转入人性恶,不惮于直面丑陋与残酷,不惜伤及优雅……”
诚然,对社会结构和都市病态人格的正视,大大拓展了张欣新世纪以来作品的现实感和人性深度。而没有下过乡,没有经历过太多人生苦难,以及对南方城市的深刻理解和热爱,并没有削弱这些作品的深度,反而形塑了张欣独特的都市写作的个性化风格。由此,她彻底完成了一次创作灵魂的“重生”。
“这是一个相当艰难和残酷的过程。”她感慨。而更多的人,未能穿越这个价值撕裂的过程,及时找到自己的路,转瞬新时代来临。面对新作家、网络写手的冲击,“不是他们不愿意,很多作家真的是突然之间就不会写了”,“这些人我说名字你们也不知道,没他们什么事了,只有有价值的人才能留下来”。
一个人的“南方写作”
有人说,一个老外如果想用最轻松的方式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南方都市生态,可以去看张欣的小说(《爱又如何》):大家都从自己原来的角色里出来转变身份去捞钱,面对这份共同的生活考卷,心态各异。
简单的“都市小说”或许也不适合成为张欣的标签,“爱情小说”当然更不靠谱,她自己总结了一个概念—南方写作。
“我一直很坚持这种书写,写我们南方。一直以来我们南方太不受重视了,话语权都在北京。但广州这个城市在北上广里其实是很有特点的,北京是很文化,上海是很时尚,广州呢,它的观念太新了,永远不陈旧。我们离香港很近,大家都知道香港的都市文化,哪怕我俩关系再好,只有一个位置的时候我肯定把你干掉,你走好过我走。接着我们没有‘隔夜仇’,下次有机会还接着合作。”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在广州我认识有人投资失败,几十万没了,我问他怎么办,他说那能怎么办啊,没了就没了,接着搞别的呗。这样的事情在内地,可能天都塌下来了—那种承受能力,那种消解能力,这就是广东。它有一种骨子里的冷漠,但也有属于自己的温情。”
“我坚持就写南方发生的故事,哪怕没人看也写。”张欣笑着说,“最后你想知道南方的生活,就只能看我写的了。”
她不时会和这个城市的其他作家朋友聊天,因为理解坚持走出自己文字之路的不易,她乐于向年轻作家分享自己的经验。“我经常和他们讲,你要做个有趣的人,不能乏味。一般不跟他们讲具体的写作,太具体了,没法讲,只讲做人、做事,以一种怎样的胸怀接受这个世界。”
广州作协每年组织的采风、讲座培训也带有她个人特质的影子:谈文学的、心理学的,和尚、收藏家都有。“我觉得年轻作家视野很重要,我也和他们一起听;知识都会老化,你要不断地听别人穷尽一生研究的东西。”
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书写冷酷,张欣最近的作品风格又有了一个转折:在《终极底牌》里,呈现都市的复杂与残酷之后,却回归了人性的温暖。
这跟社会的变化和个人内心的变化都有关系。当人们无视社会的裂变,捂着眼睛高唱真善美,希望把文学当成心灵鸦片之际,她偏要冷酷地掀开那层华丽的遮羞布;而当社会的沉沦已经一再突破底线,她反而渴望提醒人们,不要忘却内心残存的那份温暖。
更重要的是,过往书写过那么多病态的灵魂、高涨的欲望—她承认,某种程度上也是同为都市人的自己内心的阴影。“我很庆幸我能成为作家,写作疗愈了我,让我可以诚实地正视和释放了内心的负面与阴暗。”
这个时候的她,反而成为了一个重新能够相信温暖的人了,尽管在这个于她而言已经失却底线的社会里,那是如此的艰难。(甄静慧)
上一篇
写好软文广告的4个小技巧分享到:
相关动态
第八届感恩日本作文比赛获奖名单揭晓
2016-01-07 09:16
17596
近日,由人民中国杂志社和日本科学协会共同主办的第八届 「笹川杯作文コンクール 2015-感知日本」 大赛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百余所高校的学生们参加。经过专家的认真评选,最后,南京邮电大学的王喆琦同学和合肥学院的奚相昀同学获得了优胜奖,另有16名同学分获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本次参赛作品收获了许多好文章。这些文章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涉及民间交流、科技、环保、文化以及中日关系等领域,从多个视角记述了中日友好的渊源,文化差异以及对中日两国未来发展的观察与思考,反映出当代中国青年对中日发展世代友好关系的期盼与担当。 感谢日本财团并笹川阳平会长、尾形武寿理事长,以及日本科学协会大岛美惠子会长为本次大会所做的贡献;对给予支持的日本国驻华大使馆、中日友好协会、全日本空输株式会社(ANA)、大新出版集团以及对各高校老师和外教们表示感谢。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网、中国网、沪江网、中日之窗、贯通日本等媒体表...
关于美食的作文:人们为什么喜欢吃臭豆腐
2016-01-07 16:25
16574
摊主将几块豆腐放入锅里,再用长筷子不停地将每一块豆腐翻来翻去。刚放进去的时候,只见那些豆腐块像顽皮的孩子在游泳池里戏水,溅起了无数的“水花”。渐渐的,豆腐块开始变成黄色,慢慢地就鼓起来了。不一会儿,便可出锅,再浇上一些自制的调料,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臭豆腐就做好了。 这就是美味的臭豆腐,也是家乡南京最著名的特色小吃,你想尝尝吗?...
洋湖杯童眼看世界主题作文与绘画大赛获奖名单揭晓
2016-01-07 16:25
18001
2015年童眼看世界主题征文绘画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绘画:彭雅岚 低年级作文:唐暄诒 高年级作文:李雨萱 二等奖:绘画:梁伟煜、唐曼宁、段雨若 低年级作文:向启正、游文昕、彭广怡 高年级作文:任学归、游晟君、胡木菲 三等奖:绘画:张煜东、张馨尹、张乐晗、赵芷宇、胡灵珊 低年级作文:曾浩恒、刘仔顺、黄瑜、邹雨彤、周子东 高年级作文:吴玉茜、谢浪飞、易思岑、魏楚轩、陈坤豪 优秀指导老师:绘画:虫虫少儿美术教育 甘素华 ; 童年的天空绘本老师 萧翱子 低年级作文: 点赞作文 彩虹老师 ;小杜鹃艺术实验学校 何诗娟 高年级作文:中南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梁琴、黄敏 优秀奖:1、梁雅彤《舞动中的莲蓬》2、宋敏嘉《婀娜的姿态》3、彭栋杰《蚂蚁们的聚会》4、赵芷宇《飞舞的天鹅》5、唐果《背包》6、何雅褀《可爱的小奶牛》7、柏元杰《大猫和小猫》8、王梦宣《眼睛放大啦》9、吴晞墨《爱跳舞的莲蓬》10、于泽轩《放大后的世界啥样》11、刘雅欣《夜间卫士...
推荐文章

能不能用AI代写论文、代写作业?
2024-06-07

架起文学与影视沟通的桥梁(坚持“两创”·关注新时代文艺)
2023-11-24

聚焦互联网时代书店转型
2023-06-21

240万字《广东文学通史》问世!广东省作协七十芳华正青春
2023-0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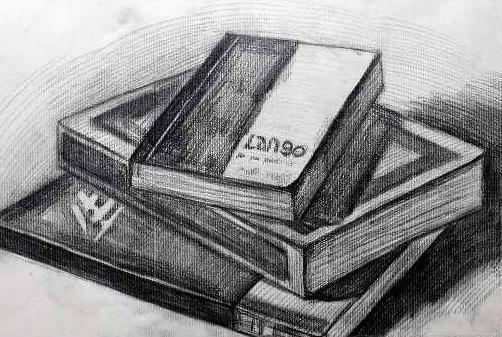
如何玩转北京国际图书节
2023-06-16